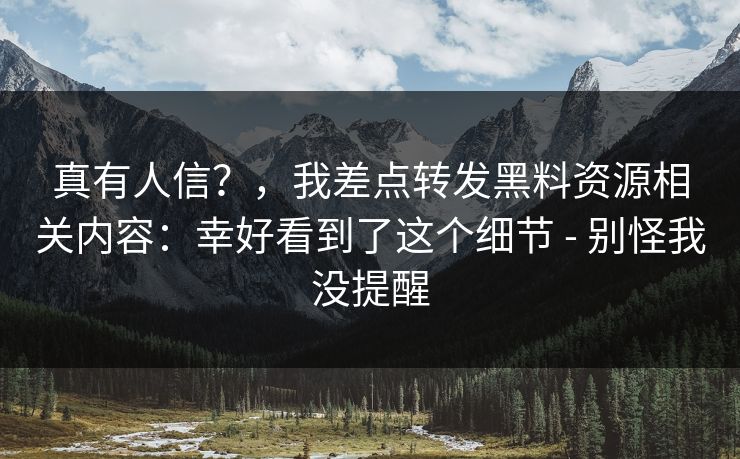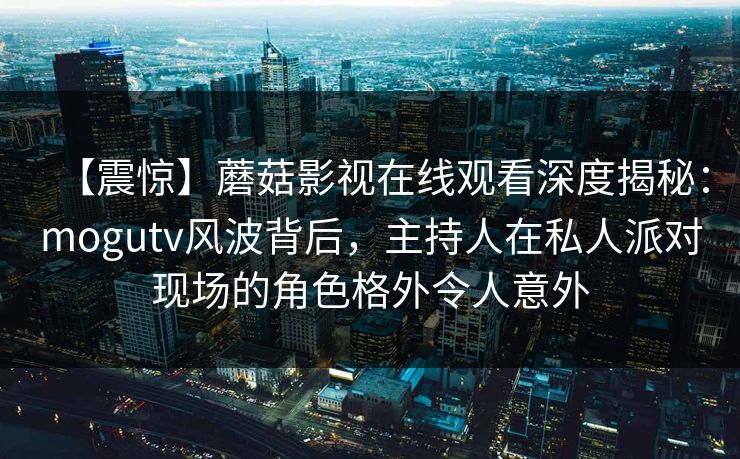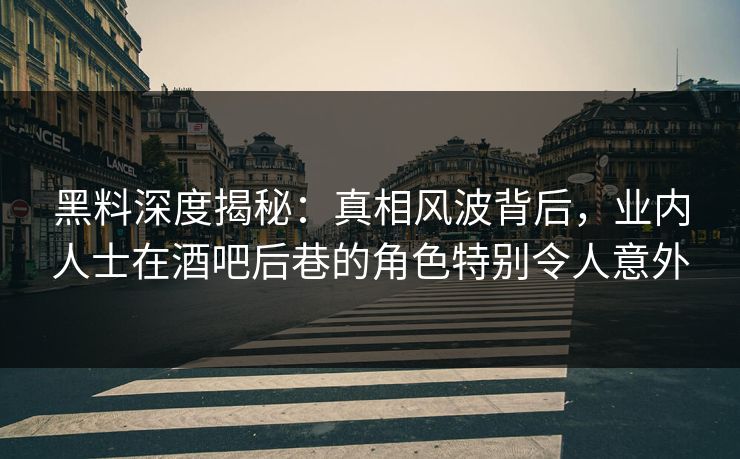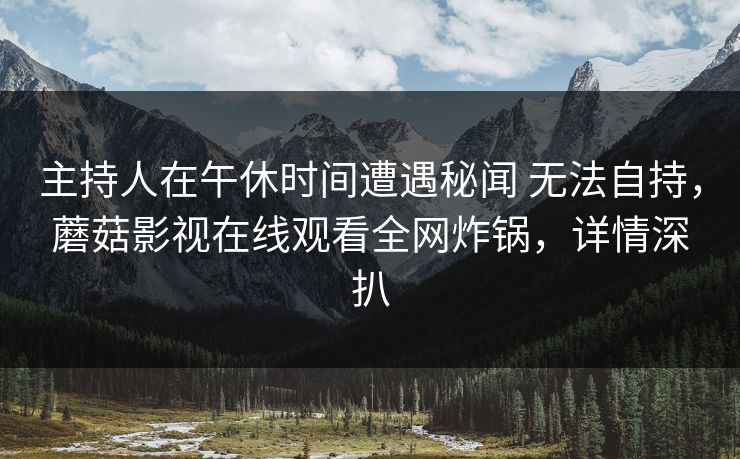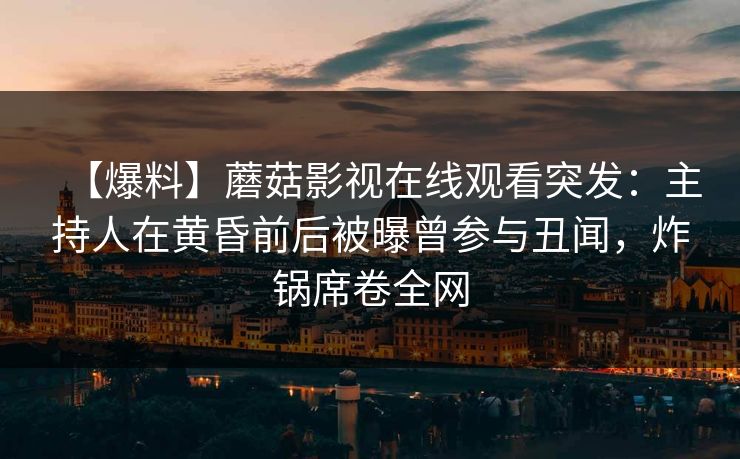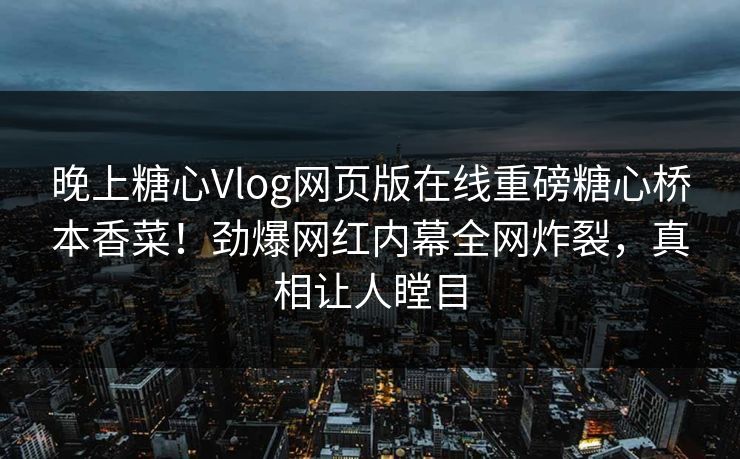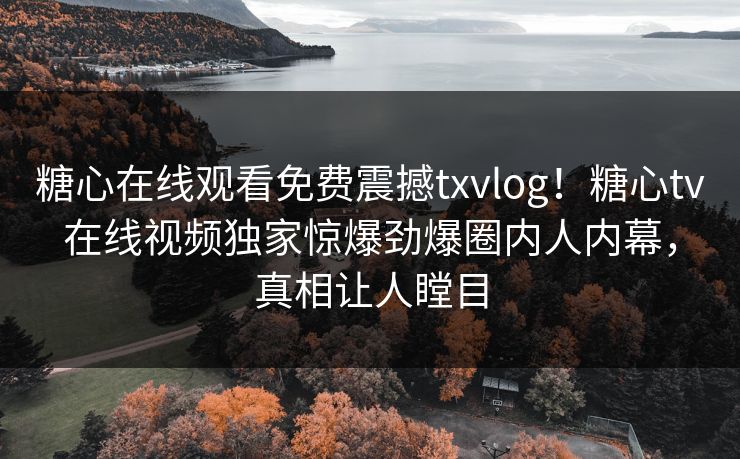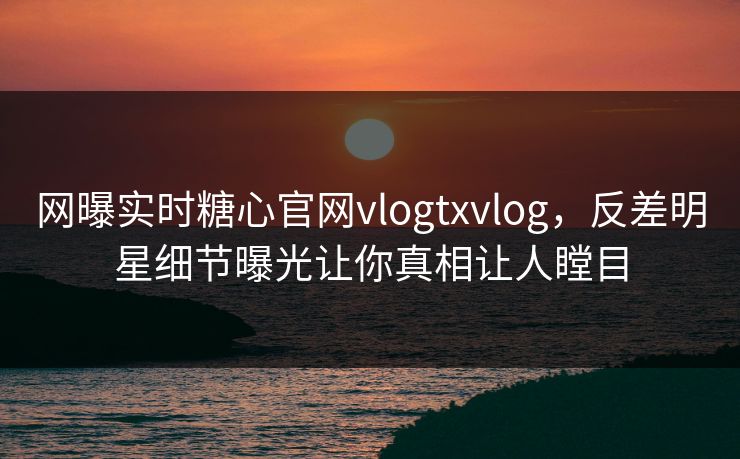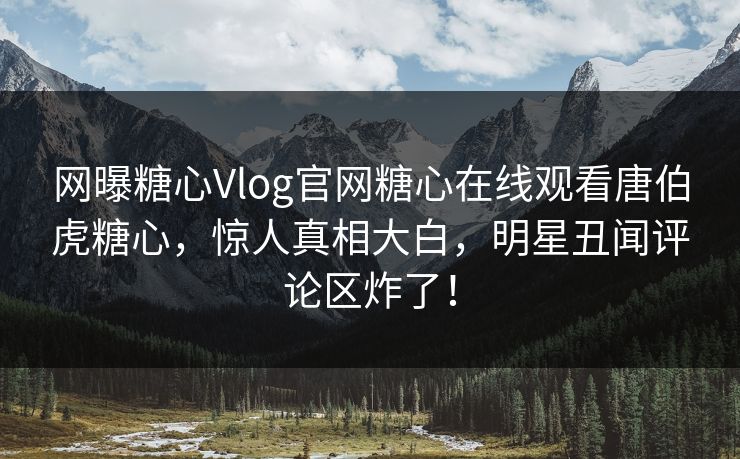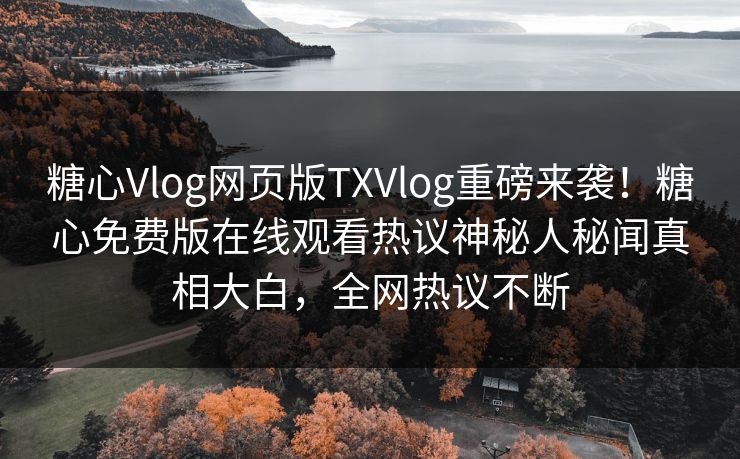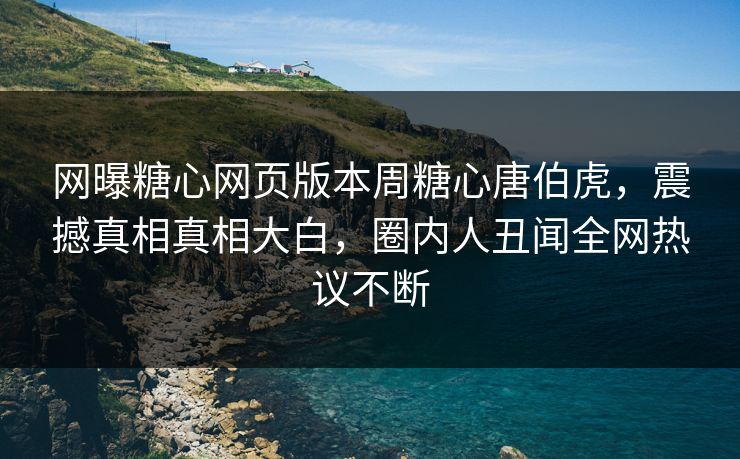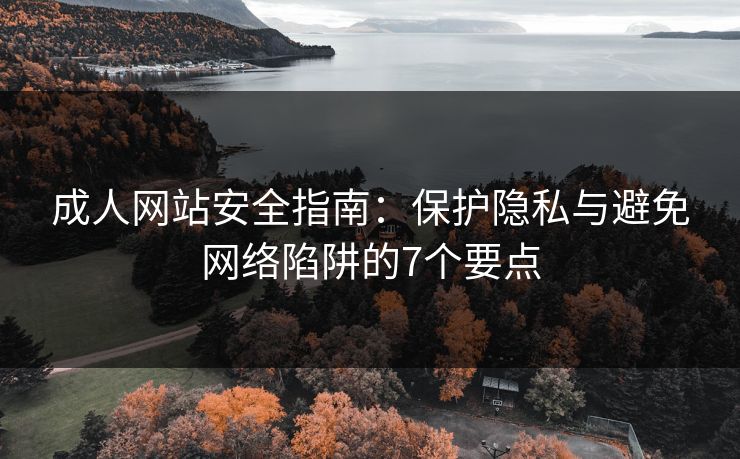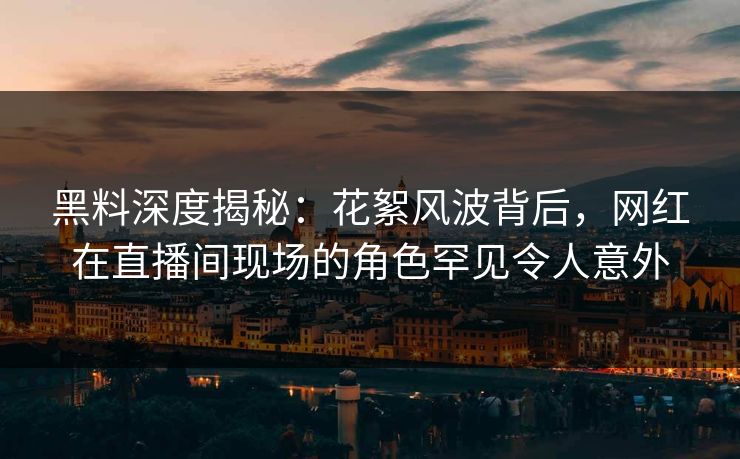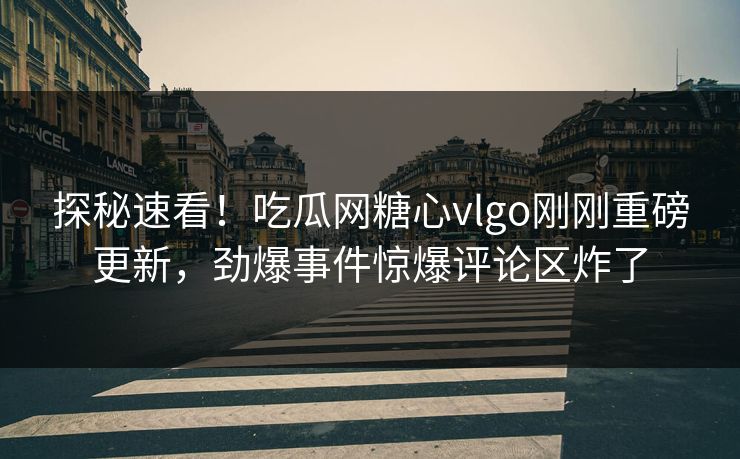当孩子说“想C”,我选择说“好”——一个母亲的放手与成长日记
一场突如其来的“叛逆”请求
那天晚上,餐桌上弥漫着番茄炒蛋的暖香。儿子小哲扒拉完最后一口饭,突然放下筷子,眼神闪烁却语气坚定:“妈,下学期……我想C。”

空气凝滞了三秒。我握着汤勺的手顿了顿——“C”是他和同学间对“换班级”的隐语。心脏猛地一沉,无数担忧瞬间涌现:现在的班级不好吗?师资顶尖、同学友善,为什么要换?是不是受了委屈?还是学习成绩下滑想逃避?
但我没有立刻反驳。我望着他紧绷的嘴角和微微发红的耳根,突然意识到:这或许不是一时冲动。十五岁的他,第一次用如此郑重的语气向我提出“非分”之请。
“说说看,”我盛了碗汤推到他面前,“为什么想C?”
他深吸一口气,像背书一样列出理由:现在的班级竞争太激烈,他总觉得自己像吊车尾;好朋友大多在隔壁班,下课想一起打球都凑不齐人;更关键的是,新班级有他向往的机器人社团,而现任班主任认为“搞科创影响学习”……
想起自己十五岁时,也曾憋红脸向父亲请求转学美术班,却被一句“成绩这么好学什么艺术”打了回来。如今三十年过去,我依然会梦见调色盘和未画完的素描。
那个夜晚我失眠了。披衣起身,翻出他从小到大的相册:幼儿园攥着我的衣角哭鼻子的一团、小学运动会摔跤后爬起来狂奔的背影、中学第一天独自打包书本的侧脸……我的孩子,早已不是需要我事事代劳的幼崽了。
第二天清晨,我把热牛奶递给他。“好。”
他愣住,睫毛颤了颤:“……真的?”“但有条件,”我微笑,“你要自己负责和两边班主任沟通,月考前进二十名,还有——”我眨眨眼,“机器人比赛得拿个奖回来。”
他跳起来抱住我,牛奶洒了一身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:所谓的“叛逆”,或许只是成长换了个样子来敲门。
放手之后,花开两朵
换班手续比想象中复杂。小哲磕磕绊绊地写申请、找老师签字、协调课程表,有次还被教务处老师训斥“瞎折腾”,回家时眼睛都是肿的。我强忍着没插手,只在睡前放了杯温蜂蜜水在他桌上。
转班后的日子如同拆盲盒。前两周他兴奋地分享新班级的趣事:幽默的物理老师会用篮球讲抛物线,机器人社团的学长带他拆解一台老式收音机;但第三周开始抱怨“化学老师讲话太快”“同桌老借笔记不还”。
我在心里捏把汗,表面却只问:“需要我帮你整理化学笔记吗?”他摇头:“我自己录了音,慢速播放听。”
转折发生在期中考试后。他举着成绩单冲进门,总分排名前进了二十八名——远超我们的约定。更惊喜的是,他所在的机器人小组拿了市级竞赛二等奖。颁奖典礼上,我看着他在台上挠头傻笑,忽然眼眶发热。
这场“冒险”改变了我们两个人。他学会了为自己选择负责,而我学会了倾听比指导更重要。如今他依然会突然蹦出些“想D”“想E”的念头——可能是想染发、学街舞或者暑假去支教——我不再条件反射地说“不行”,而是坐下来问:“仔细说说?”
有时我会想,亲子关系像放风筝。线握得太松,风筝会坠毁;攥得太紧,又飞不高。那个说“想C”的夜晚,我选择松了松线,却发现他迎着风飞得又稳又远。
现在他常调侃:“妈,你当时不怕我学坏吗?”我笑着揉乱他头发:“怕啊!但更怕你变成不敢说出‘想要’的大人。”
养育孩子终归是一场得体的退出。而那句“好”,是我们共同长大的开始。